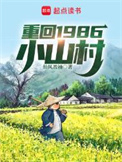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煮酒论史篇】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 作者钱穆(3/5)
门第,做过好几任宰相,直到明末,还是几百几千家聚族而居。
他看见这样的村庄,他认为社会要封建才得有力量。
外面敌人来了,纵使中央政府垮台,社会还可以到处起来反抗。
但他所讲的封建,却并不是要特权,只是要分权。
中央早把权分给与地方,中央垮了,地方还可有办法。
这是顾亭林的苦心。
再一位是孙中山先生。
他要革命,他跑到外国,只结合一些知识分子,这是不够力量的。
他看见中国社会有许多帮会和秘密结社,他认为这是中国社会一力量,可以利用。
这种帮会组织,自然不能说它是封建,也不是资本主义。
当知只要有组织,便可有力量。
我们看西方,一个大工厂,几千几万人,有的政党便尽量挑拨利用,闹起事来,一罢工就可发生大影响。
因为是一个组织,所以是一个力量了。
中国近代社会却找不出这些力量来。
人都是平铺的,散漫的,于是我们就只能利用到学生罢课,上街游行,随便一集合,就是几百几千人,这也就算是力量了。
西方由封建主义的社会进到资本主义的社会,不过是由大地主变成大厂家,对于群众,还是能一把抓。
在此一把抓之下,却形成起力量来。
中国传统政治,向来就注意节制资本,封建势力打倒了,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
若要讲平等,中国人最平等。
若要讲自由,中国人也最自由。
孙中山先生看此情形再透彻没有了。
然而正因为太过平等自由了,就不能有力量。
平等了里面还有一个关键,就是该谁来管政治呢?政府终是高高在上的。
社会平等,什么人该爬上来当官掌权呢?中国传统政治,规定只许读书人可以出来问政,读书人经过考试合格就可坐观。
读书人大都来自农村,他纵做了官,他的儿孙未必仍做官,于是别的家庭又起来了,穷苦发奋的人又出了头,这办法是好的。
不过积久了,读书人愈来愈多,做官人也愈来愈多,因为政权是开放的,社会上聪明才智之士都想去走做官这条路,工商业就被人看不起。
西方社会就不通,起先根本不让你做官,实际纵使封建贵族,也没有所谓官。
于是社会上聪明才智之人都去经营工商业,待他们自己有了力量,才结合着争政权。
这就形成了今天的西方社会。
中国很早就奖励读书人,所谓学而优则仕,聪明人都读书,读了书就想做官去,所以使中国政治表现出一种臃肿的毛病。
好像一个人身上无用的脂肪太多了,变肥胖了,这不是件好事。
但这现象,直到今天,还是扭转不过来。
第三:长治久安,是人人希望的,可是在这种情形下的知识分子,至多也只能维持上三代。
起先是一个勤耕苦读的人出来问世,以至飞黄腾达,而他的下一代,很快就变成纨绔子弟了。
于是有另一个家庭里勤耕苦读的人物,又再昂起头来。
我们只看宋明两代的宰相,多数是贫寒出身,平地拔起的。
然而天下太平,皇帝可以两三百年世系着,做宰相的人,前十年还在穷乡茅檐下读书,但皇帝已是有着七八世九十世的传统了。
相形之下,皇帝的地位和尊严,自然一天天提高。
皇室的权,总是逐步升,政府的权,总是逐步将。
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上的大毛病。
虽说此后这一毛病可以没有了,但读历史的仍该知道这回事,才能对中国以往政治有一种比较合理的认识。
第四:是中国的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
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订一个制度来防制它,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
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缚。
这一趋势,却使中国政治有后不如前之感。
由历史事实平心客观地看,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而西方近代政治,则比较偏重在人治在事实化。
何以呢?因为他们一切政制,均决定于选举,选举出来的多数党,就可决定一切了。
法制随多数意见而决定,而变动,故说它重人、重事实。
我们的传统政治,往往一个制度经历几百年老不变,这当然只说是法治,是制度化。
法治之下,人才就受束缚了。
所以明末的黄梨洲要慨然说:“有治人,无治法。
”这因一向制度太繁密,故使他太不看重法,太看重人,而要提出此主张。
但尚法并非即算是专制,而中国历史上平地拔出的人愈后愈多,而自由展布之才,却愈后愈少了。
此后的我们,如果不能把这种传统积习束缚人的繁文琐法解放开,政治亦就很难有表现。
刚才我们讲,中国社会上想从政做官的人太多了,但又再加上这些法令制度的繁密,来重重束缚他,这就是中国政治没有起色的根源。
今天我们的政治,已经走上一新路,似乎以前历史上的往事,可以一切不问了。
其实这观念还是错误的。
传统政治的积弊,虽是历史,同时也还是现实。
外貌变了,实质仍未变,如何能不仔细研究呢?正如我们误认了以往政治传统一切该打倒,而且也真的一切被打倒了。
同时我们对一切传统和习惯,也失去了共尊共信新。
几千年的皇帝打倒了,政治变了新花样,但无论如何,不得不先求国家之统一。
要求统一,便要中央集权。
但中央威信如何能建立,这就成为辛亥以来政治上一个大问题。
我们若拿不出一个为全国人民共尊共信的东西来,这工作自会感觉到困难。
而且建立中央,同时又须顾及地方,这不是更困难了吗? 上面我们说过,中国社会早已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所以在这个社会里的一切力量都平铺散漫,很难得运用。
因其是平铺的,散漫的,因此也无组织,不凝固。
然而我们面对着同一事实,却往往讲两样的话。
一方面说我们是封建社会,一方面又说我们是一盘散沙。
不知既是封建,就不会像散沙。
既说是一盘散沙,就证明其非封建。
但我们的将来,要是不走上西方资本主义的路,那么我们又如何来运用我们将来的新政,使社会再有一个新的共尊共信之点而向此中心再度凝结呢?这又是今天政治上极重要的一件事。
现在皇室是推倒了,皇帝是没有了,我们只说政治的主权在民众,现在是民权时代了。
可是就实际言,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哪能立地真来操纵这政权呢?孙中山先生说:此四亿五千万人都是刘阿斗,这话再正确没有,因此他主张在政治上的权和能要分开。
孙先生不是读死书的人,他这几句话,并不由任何西方抄袭来,他真是深识远虑,确有他所见。
政府是该属于民众的,但不是,也不能,定要全体民众直接来掌握此政权。
理论上,国家政权当然在民众,该以民众大家的意见为意见。
但民众意见,终是句空话。
如何来表达出此民众的意见呢?今天中国多数民众,尚依赖政府来注意教和领导,他们哪有办法来过问政治?然而一个国家总要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中心,即如目前的日本,他们把历史上的传统中心皇帝尊严摇动了,急切间社会也会发生摇动的,他们拿什么东西来填补,来维系?这在他们也将成为一问题。
中国也会碰到这问题的,而且早已碰到了。
我将最后申说着一点。
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使人才能自由发展,这是最关紧要的。
但这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功。
重要的不在推倒,在建立,我们说,我们要建立法治,现在我们的文书制度,层次之多,承转之繁,使人一跑进这圈套,就无法得转身。
再加上民主二字,好像什么事都待集体商量过,于是文书递转以外再加上开会忙。
照目前情形,只要开会和递转文书,已够使每一个人在政治上不能表现出才能。
我们天天说我们的法不够,其实不够的不在法,而在才。
这也不是我们之无才,乃是我们的才,不能在我们的法里真有所表现。
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人才,也总有一个时代的法制。
人才无可表现,于是有大乱。
若专要法制来束缚人,使人人不获尽其才,则必将会酿乱。
我们现在将如何酌采西方的新潮流,如何拿自己以前的旧经验,来替自己打开一出路,来创新发,运新才,这当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政治确实是一件麻烦事,就近代历史看,算只有英国政治支撑了几百年,此外都是几十年一百年就垮台了。
我们不能专看别人家,样样向人学。
人家的法规制度,同样不能有利而无弊。
但人家各自在创制,在立法,他们觉悟到有了毛病,还可改。
我们则一意模仿抄袭,就更没有所谓觉悟了。
英国的政治比较能持久,然而我们是大陆国,广土众民,他们是岛国,国小民寡,我们又怎能全盘学他呢?美国由英国分出,已不全学英国。
法国政治传统也较久,但此刻已不行。
此外像德国、意大利、日本,我们竟可说他们还没有可靠的政治经验。
若我们更大胆说一句,也可说整个西方人在政治经验上都比较还短浅。
能讲这句话的只有中国人。
中国政治比西方先进步,这是历史事实,不是民族夸大。
这句话也只有孙中山先生曾说过。
今天我们要反对中国自己传统,想要抹杀我们自己两千年历史,但历史已然成为历史了,如何能一笔抹杀呢?别人家自有别人家的历史,我们又如何能将自己横插进别人家的历史传统呢?这又牵涉到整个文化问题了。
纵论及此,便见是非常复杂了。
我不敢在这里空谈理论,只能讲历史。
当前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过:讲哲学,都可叫人不武断。
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
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
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
至少我们讲人文科学方面的一切,是不该不懂历史的。
政治也是人文科学中一门,我们回头把以前历史经过,再看一道,总还不是要不得。
钱穆年表 1900七岁入私塾读书 1903十岁进果育小学就读 1905十二岁父逝 1906十三岁入常州中学堂 1910十七岁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适逢武昌起义,学校停办,遂辍学 1911十八岁任教无锡三兼小学,为教学生涯之始 1918廿四岁任教鸿模学校,即原果育小学,出版《论语文解》 1919廿五岁任后宅泰伯市初小校长 1922廿八岁赴厦门任教集美学校为任职中学教师之始 1923廿九岁任教江苏省无锡第三师范学校 1927卅三岁转任教苏州中学 1928卅四岁妻殁、儿殇、兄亡连遭三丧 1930卅六岁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后任教北京燕京大学为任教大学之始 1931卅七岁任教北京大学历史系,并兼课清华、燕京、北师大 1935四一岁出版《先秦诸子系年》 1937四三岁随政局南迁,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1939四五岁《国史大纲》脱稿,回苏州侍母一载 1941四七岁往成都任教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及武汉大学 1943四九岁先后任教于华西大学、四川大学 1944五十岁撰文《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号召知识分子投笔从戎 1946五二岁赴昆明任教五华学院、兼任云南大学 1948五四岁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课余撰《湖上闲思录》 1949五五岁赴港任亚洲文商学院院长 1950五六岁成立新亚书院、应邀赴台讲演 1951五七岁为筹办新亚书院台湾分校滞台数月,未果。
1952五八岁4月,在淡江文理学院惊声堂讲演,屋顶泥块坠落击中头部晕厥送医。
1955六一岁新亚研究所成立,访日,“教育部”颁赠学术奖章香港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1956六二岁新亚书院农圃道校舍暑期落成,为自有校舍之始与胡美琦女士九龙缔婚 1957六三岁新亚书院增设艺术专修科 1960六六岁赴耶鲁大学讲学,课余撰《论语新解》耶大颁赠名誉博士学位后赴欧访问 1961六七岁新亚书院理学院成立 1963六九岁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曾辞新亚书院院长职 1965七一岁正式卸任新亚书院院长,离港赴吉隆坡马来亚大学讲学 1967七三岁十月迁居台北 1968七四岁迁入素书楼,膺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9七五岁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故宫博物院”聘为研究员 1974八十岁撰《八十忆双亲》 1976八二岁是年冬,胃病剧作,几不治 1978八四岁该年常病,目不能视,抱病赴港任新亚书院‘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主讲人。
1979八五岁赴港出席新亚三十年纪念会 1980八六岁与三子、幼女会于香港,卅二载未见,得七日相聚 1981八七岁与长女、长侄晤聚香港,五子女两年内分别见面 1984九十岁获颁行政院文化奖章 1986九二岁为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学生上最后一课 1988九四岁在家中授课至是年方休 1989九五岁赴港参加新亚四十年纪念会 1990九六岁六月一日迁出素书楼八月卅日逝于杭州南路寓所 1992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 钱穆先生小传 钱穆先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初九(公历7月30日)生于江苏无锡,于1990年8月30日卒于台北,享年96岁。
这位世纪老人以其博学精思、著作等身而享誉世界,是本世纪中国不可多得的一位国学大师、著名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钱先生原名恩,字宾四,民元(1912年)改名穆。
钱家世居江苏省无锡县南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村。
七房桥以钱家先世七房受名。
钱穆曾祖绣屏为国学生,祖父鞠如为邑生。
祖父治五经和《史记》。
穆父承沛,字季臣,幼时有神童的美称,16岁时县试,考取第一名为秀才,由于身体多病,未求取功名。
母蔡氏,乡里称淑德。
钱穆有一兄一姐两弟。
钱穆七岁入私塾,十岁进无锡荡口镇私立果育小学。
四年间得到良师钱伯圭、华倩朔、华紫翔、华山、顾子重等先生的民族精神、人文素养的启发、获益匪浅。
钱穆十二岁时遭父丧,家徒壁立,靠本族怀海义庄抚恤为生。
他十三岁考入常州府中学堂,深受校长(时称监督)屠孝宽的爱护。
历史、地理老师吕思勉的教诲对钱穆影响很大。
1910年冬钱穆因故退学,次春转入南京钟英中学读书。
辛亥革命爆发后,学校被迫解散,钱穆辍学回乡,从此结束了他的学生时代,开始了乡间教书的生涯。
1912年,钱穆十八岁,任教秦家水渠三兼小学。
次年任教鸿模小学(其前身为果育小学),教高小国文、史地课程。
他研读《孟子》、《史记》和毛大可的《四书改错》,又喜读《东方杂志》和严译数种。
时钱穆以未上大学为憾,见北京大学招生广告说投考者须先读章学诚《文史通义》,即求其书读之。
他又读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因其为北京大学教本,故读之甚勤。
他后来著《先秦诸子系年》,订正《史记·六国年表》,即是受夏书的启发。
1914年夏,钱穆任教设于梅村镇的无锡县第四高等小学,同时兼任鸿模小学的课。
一年后才专在县四高小任教。
在繁忙的教书工作之余,坚持读书,效法古人“刚日读经、柔日读史”。
钱穆授《论语》课,正好在读《马氏文通》,即仿其例论句法,成《论语文解》。
是书1918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是钱氏之第一部著作。
又读《墨子》,发现多处伪误,成《读墨解》。
后询悉孙诒让有《墨子诂》,才自知孤陋,于孙书逐字细读,并自此留心清代考据之学。
钱穆因读严译《穆勒名学》有得,故对孙氏解《墨经》之未尽惬意处,逐条改写,成《墨经解》。
1917年秋,钱穆完婚。
1918年是钱穆读书静坐最专最勤的一年。
1919年秋天,钱穆任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校长,时年二十五岁。
他受杜威教育思想影响,企望通过与幼童接触,改革教法,并试一试白话文对幼童初学的利弊得失。
此期间得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石印本一册,是他以后写《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张本。
1922年秋,钱穆辞去后宅小学校长及泰伯市图书馆长之职,到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任教。
不到一个月,应施之勉教务长之聘,到厦门集美学校任高中部与师范部毕业班国文教师。
1923年,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资深教席钱基博先生荐钱穆至同校任教。
学校旧例,国文教师随班递升,国文一科外,每年必另开一课(第一至四年分别开文字学、《论语》、《孟子》、《国学概论》,教者自编讲义)。
钱氏的《六书大义》、《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国学概论》即编撰于斯,后三种均出版。
1927年秋,钱穆执教苏州省立中学,任最高班国文教师兼班主任,为全校国文课主任教席。
1928年春为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作《墨子》和《王守仁》。
是年夏秋之际,钱穆的原配夫人及新生婴儿相继去世。
他的长兄声一先生赶回家帮助料理后事,因劳伤过渡,旧病突发,不幸也病逝。
两月之内,连遭三丧。
钱穆在苏州中学期间,课外主要研究工作为撰写《先秦诸子系年》。
1929年,钱穆与张一贯结婚。
是年,顾颉刚、胡适相继来苏中演讲,钱穆得以与顾、胡相交。
顾颉刚读到《系年》初稿,建议钱氏到大学教历史,并向中山大学推荐。
钱氏虽获中大致聘,但苏中校长汪懋祖恳请钱再留一年,逐不果行。
钱与蒙文通曾通信论学。
1930年蒙文通在南京讲学,曾来苏州与钱相见,畅谈数日。
蒙文通赞誉钱之《系年》可与顾享林诸前贤的论著相媲美,认为“乾嘉以来,少其匹矣”。
由于顾颉刚的推荐,1930年秋,钱穆得以任北平燕京大学讲师,讲授国文,时年三十六岁。
从此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大学教书生涯。
是秋,恰逢刊载了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的《燕京学报》第七期出版,此文亦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夸夸我的神探祖父穿越爹渝跃鸢飞
- 红男绿女常书欣
- 阴阳执掌人洛冰
- 咸鱼女配在恋综躺平后爆红阿堃
- 无限轮回荣光九四或跃在渊
- 撩肾达人/万千荣光甜醋鱼
- 我在东京教剑道范马加藤惠
- 关小姐又在写情书茴笙
- 超神宠兽店古羲
- 我在古代当先生北沐南
- 绯闻之王期待崛起
- 给卫莱的一封情书梦筱二
- 大宋有毒第十个名字
- 我靠造梦制卡爆红联邦清蒸胖鞋
- 墨道归元胡鳕
- 雪下轻卿[先婚后爱]州府小十三
- 桃花折江山白鹭成双
- 和豪门大佬隐婚后林多多
- 身为女王如何拒绝爱意吾九殿
- 大唐不良人庚新
- 拜托,只想干饭的北极熊超酷的!弦三千
- 原谅她范月台
- 七十年代奇葩一家亲永岁飘零
- 醒日是归时含胭
- 遮天辰东
- 大明话事人随轻风去
- 离婚后,我能听到未来的声音林中谷
- 我的18岁男房客Antigravity
- 军工大院女儿奴[年代]浣若君
- 恶魔家灵感界主
- 始皇家养小皇后林宴歌
- 当药族仙女来到星际余夕婪乔松
- 引诱(志怪1v1 h)渐无书
- 返龙柿子的猫
- 欢喜记石头与水
- 刑侦专家她在90年代当未成年七七笙
- 荒野求生种田手册一叶霜寒
- 我大哥也穿过来了!阿扶光
- 清纯炮灰连夜跑路喻狸
- 在西汉庖厨养娃万重泉
- 美莉栗优
- 假千金回山村后(美食)山早早
- 婚后生情慕思在远道
- 你在说什么啊啊啊!梨橙橙
- 演替半截白菜
- 不是人又怎样[快穿]宴不知
- 穿越玄幻最强反派:觉醒返利系统麟双
- 北域战记五江半岁生
- 港城经营日记[西幻]李念月
- 退役勇者转职魅魔sanna
- 为我心动[无限]洛大王
- 丧尸老公喂养日记岩城太瘦生
- 糟!我老婆外面有狗了山有青木
- 欢喜记石头与水
- [西幻]北道而驰爱因斯弹簧
- 荒野求生种田手册一叶霜寒
- 别人航海,我种田风的铃铛
- 暧昧掌控十九行诗
- 演替半截白菜
- 我的物品能升级全针教主
- 沉迷种田,我爆红全网home毒步天下
- 贼天子漫客1
- 暗恋的邻居是兼职杀手好伞
- 万人迷症候群[快穿]蒲中酒
- 目标是末世最强BOSS万玖
- 给娱乐圈一点万人迷震撼!须补
- 炮灰,但在美校谈恋爱夭甜怡
- 寻宝全世界行走的驴
- 吞噬星空2起源大陆我吃西红柿
- 异界之三国群英传灭世小苹果
- 我!清理员!鱼狱圄
- 我靠画像破案成了警界瑰宝[刑侦]豆子禹
- 我被困在方块之中狂喜
- 她是风暴中心油油泼泥
- 守寡多年[星际]芝芝猫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