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煮酒论史篇】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二) 作者钱穆(4/5)
于内阁。
若内阁和六部发生意见,六部可以说:你不是宰相,不是大臣,不该管我们的事。
不该管的事而管,不该揽的权而揽,此是权臣,非大臣。
权臣弄权与大臣当权,在中国传统政治观点上是大有分别的。
大臣是在当时的制度上有他正当的地位的。
在中国传统制度下,宰相无事不该问,无权不该把。
他不问事,不当权,是失职,是无能。
并非宰相,而问事揽权,是奸臣,是权臣。
权臣弄权,这是违反国法的,也是违反政治上的传统道德的。
然而明代的制度,则根本没有一个正式的宰相。
六部尚书乃及七卿九卿,始是名正言顺的大臣。
当时反对张居正的人,他们心里想:部(六部)院(都察院)长官,分理国事,只受皇帝节制,你做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私人顾问,你在皇帝面前,“从容论思”是你的责任,你不该借着这一点关系正式出面来干涉部院,那是你越权。
因为张居正要管事,所以他要各衙门奏章公事每样备两份,一份送内阁,一份送六科给事中。
这又是他不对。
给事中虽官阶低,但在当时政制法理上,一切文件,该他过目,这是不错的。
内阁则并无必须预闻之职权,只皇帝私下要他预闻才预闻。
所以当时人反对张居正,张居正市没有理由答辩的。
他于是只有向皇帝去辞职,他说他“所处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这几句话,丝毫也不错。
然试问当时何尝有一道正式命令叫张居正代理皇帝呢?依照中国政治传统,皇帝不该干预宰相的事,此在讲汉、唐、宋三代政制时,已详细述及了。
现在是内阁不得干预皇帝的权,就明论明,是不错的,张居正也无法自辩。
现在我们不了解当时这情形,总认为张居正是一大政治家,他能主张讲法治,其实他本身就已违法了,而且违反了当时国家的大本大法呀。
该皇帝管的事,他来管,那岂非不法之至吗?若张居正在汉唐宋三代,那是一好宰相。
依明代制度论,张居正是一内阁学士,不是政府中最高领袖,不得以内阁学士而擅自做宰相,这是明代政制上最大的法理,也是明代之所以异于汉唐宋传统的。
张居正要以相体自居,他一死,他家就被抄了。
虽然他在明代有很大的建树,但当时清议,并不讲他好话,这就因为认他是一个权臣,非大臣。
这不是专就他功业言,而是由他在政府之地位上的正义言。
此刻我们要提倡法治,却又来推尊张居正,这正为不了解明代政治制度。
当知明代的政治制度,早和汉、唐、宋传统有了很大的变化。
张居正并未能先把当时制度改正,却在当时制度下曲折谋求事功,至少他是为目的不择手段,在政治影响上有利弊不相抵的所在呀!我们以上的说法,只就制度与法理论,不从事业和居心论。
至少在当时那些反对派的意见是如此。
我们详细讲述这一层,正为阐明制度如何牵制着人事,而明代此项制度之要不得,也就即此更可论定了。
丙、明代地方政府 地方政治一向是中国政治史上最大一问题。
因为中国国家大,地方行政之好坏,关系最重要。
明代亡国以后,当时有两位大史学家,痛定思痛,来讨论明代政治制度,和此下中国政治的出路。
一位是黄梨洲,他著了一部《明夷待访录》,他最注意的是明代废宰相那一事。
他认为将来只有再立宰相,正名定义,把宰相来做政府领袖,不要由皇帝亲揽大权。
另一位顾亭林,著有一部《日知录》,他曾说: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
他举了历史上许多例来讲。
总而言之,地方政治干得好,天下就太平。
地方政治干不好,天下就大乱。
他们两人的着眼点,一上一下,各有不同。
黄梨洲注意在上面,顾亭林注意在下面。
但我们若细看全部中国政治史,便知他们两位所说,同样是颠扑不破的教训。
从中国传统历史意见论,地方政府制度最好的要推汉代,但唐代地方制度也还好。
让我们举一例来说:中国地方这样大,现在有飞机、火车、电报,政令传达,不感觉多么的困难。
从前交通完全靠驿骑,这就不容易。
驿路可通全国,到处都有站,当时则叫做亭。
唐代首都在长安,若要发一公文到番禺(广州)或者到杭州与福州,都非常困难的,这我们可以想象到。
但当时并不曾因交通之辽远,递讯之困难,而政事上有所失误。
当时公文,也分缓急等次,好像现在发电报要分加急电和普通电一样。
当时递送某种公文一点钟马该跑多少路,都有一定的规定。
从这一站到那一站,快的多少时,慢的多少时,都规定了。
每站都有守站的人,送公事的到达了,守站的早把吃的喝的都预备好,此人吃饱喝够,稍稍休息,再换一匹预先喂好了的马,继续跑。
第一天到什么地方歇,第二天到什么地方歇,都有限定。
因此几天内,如限赶到,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打电报利用科学,从前全靠人力马力。
每天户部吏部,尚书各部都有公文送往各地,一匹马来,一匹马去,络绎于路。
现在的火车轮船,有时还误点,古时驿骑误点,更该是寻常事。
但也总得多少照规定时限到达。
否则,政事就会乱,国家就会垮台。
举此一例,便知现在我们所喜欢说的中国人一向没有时间观念那句话,也不尽正确呀。
照理论,空间愈大,时间愈紧要,中国人若无时间观念,不该能统治管理偌大的空间。
再说那些站,建筑也极讲究。
假山、水池、亭阁、厅房、洗澡间、马房,一应设备都周全。
送公事的到了,总给你休息得很好,好让你明天再精神饱满地上路。
即使不睡觉、不过夜,休息一两点钟,也足够恢复你疲劳。
同时替你准备好新马,给你继续上路。
马力也分等级,携带第一等紧急公文的,便给你第一级快跑的马骑。
这些荒山穷谷的守站人,也决不会误你事。
由这一个例,可见当时行政效率之高。
但这种功绩,并不能全归之中央,这不是宰相和工部尚书的事,而是地方政府的事。
顾亭林亲自走过的地方着实多,据他说:只要看见一条大路,路基铸得坚实平坦的,询问查考,多半是唐代留下来。
只要看见一座大城,坚厚雄壮,一经询问查考,也多半是唐代留下来。
驿亭的建筑遗址,顾先生也看得多了,他才追怀到唐代的规模。
据他《日知录》所讲,真好像近代欧洲人眷念推崇罗马古迹般。
但罗马是帝国主义者征服四周,一切为武力而措施。
唐代则完全是地方政治之完善。
两者间用意不同,而顾先生也不是漫无用意,如考古家般来赞扬唐代。
他的用心,正在针对着明代之实际情况。
让我们继此来讲一讲明代的地方行政吧! 丁、元明以下之省区制度 要讲明代地方行政,最重要该首先提到的,就是现在的所谓省区制度了。
今天我们还用着行省这名词。
行省制度,不始于明代,这是从元代开始的。
也可说金代先已有行省了。
但正式成为制度的是元代。
我们今天俗称江苏省、浙江省,省像是地域名。
但历史上省字原始是衙门名,非地域名。
在金元两代,开始有行中书省。
中书省是当时中央的宰相府,一般称为都省。
行中书省是由中央宰相府(都省)分出一个机关驻扎在外面。
这因蒙古人征服中国,不敢把政权分散,要完全把握集中在中央。
某地方出了事,就由中央宰相府派一两个人去镇压,行省是一个行动的中书省。
过去御史台派人考察地方行政,今天在这里,明天到那里,所以有行台。
中书省是中央政府最高机关,怎样可以分一部分在江苏,又分一部分在广东呢?这是元代一个极不合理的制度。
这因异族征服了我们,跨驾在我们头上。
最先使用这一制度的还是“金”。
不过无论是金或元,都是外族用此制度来统治中国,都是不放心把政权交给地方,也不放心把政权分散。
所以连地方政事,也由中央政府最高领袖来亲自统治。
此如现在英国在香港,过去在印度,都设有总督,殖民地总督是直属皇帝的。
在名义上,殖民地总督,由英国皇帝派,不由内阁派。
此因内阁代表国会,国会代表民意。
殖民地根本不许有民意。
英国本土可以有民主,有自治,像香港、印度殖民地等便不能有民主与自治,所以也不该有地方官,直由皇帝派一总督来管理。
可见任何一制度,其背后都有意义可说。
元代的行中书省,就是一个行动的中央政府,宰相府的派出所,分驻在这个地方来管事。
如是则地方绝无权,权只在中央。
元代是有中央无地方的,中国只是其征服地,像英国的香港。
元朝同宋一样,把地方分成路、府、州、县,而实际上元代的地方政权不交在地方,乃由中央派行中书省管理。
行省长官是中央官而亲自降临到地方。
在当时,并不是说把全国划分成几个地方行政区,乃是这几区地方各驻有中央宰相,即成为中央宰相府的活动分张所。
所以行中书省正名定义,并不是地方政府,而只是流动的中央政府。
换言之,是中央侵入了地方。
中央需要派一个大员来镇压某地方,就派一个外驻的宰相。
在元代,共计有如是的十个分张所,并不是全国地方行政分成为十个区。
行省制度在法理上的实际情形是如此。
再深一层言之。
这种行省设施,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行政方便,而是为了军事控制。
行省制度的历史来源确如此。
所以直沿袭到近代,依然有其痕迹可寻。
我们现代的省区分划,和唐宋时代的道和路都不同。
如江苏:徐州是一个军事重镇,它一面是山东,一母是河南与安徽。
徐州属江苏省,但它的外围,江苏管不着,如是则江苏的总督或巡抚就无法控制了。
南京也是一军事重镇,但如广德不守,或者芜湖放弃了,南京也不能保,而广德、芜湖也都不在江苏的管辖内。
任何一省都如此。
给你这一半,割去你那一半。
好使全国各省,都成支离破碎。
既不能统一反抗,而任何一区域也很难单独反抗。
这是行省制的内在精神。
元代这一制度,明朝人自然懂得它用意。
明代人明知这一制度在名义上就说不通。
而且明代也废去了中书省,更何来行中书省?所以把行省长官改成为承宣布政使。
全国正式划分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
使是指的官,司是指的衙门。
我们若正名讲,该说明代的地方行政分成为十三个布政使司,不该说它分成了多少行省,或说多少省。
到清代,在承宣布政使之上,又常设有巡抚和总督。
巡抚总督在明代是非常设的官,故地方行政首长之最高一级是布政使。
但称布政使司为行政区域,已经是名不正,言不顺。
就官制言,地方区域,也不该称为司。
而清代则更无适当称呼,于是仍沿袭称了省。
譬如有江苏布政使,有江苏巡抚,而江苏地区则称为江苏行省或江苏省。
清代一统志是这样称呼的。
其实省的称呼,更是名不正言不顺。
又清一统志把省区再综合划分,如称关东三省(山海关以东),或岭南三省(广东、广西、福建)之类。
这更是无意义。
这是把政治地理和自然地理混淆了。
后来中国人果然为此误事。
别的不管,只叫广东省、广西省,不说岭南三省,或南三省,而独关东三省因为清代限制中国人出关,常把来混合称为关东三省,不分开,而后来又把关字省了,只叫东三省。
习俗相沿,好像东三省和其他省区有不同,全国只知道有一个东三省,却不看大清一统志,岭南也有南三省。
其他省区全都如此并合称呼,东三省并不和其他地区有两样,而我们却误认它是两样了。
后来又有人把东三省误叫为满洲,这更大错特错。
满洲只是吉林省松花江外长白山附近一小区域,在明代属建州卫,唐称府,明称卫,这是军事区域的名称,并不是东北的行政区域。
关东三省,才是东北行政区域,而尚不全是行政区域。
而一般人不注意这些事,或者满洲人要故意把满洲两字的地域观念放大,所以他把省区也勉强分为关东几省,岭南几省等不合理的称呼,来牵强混淆。
而后来日本人又推波助澜,故意把东三省说成是另外一区域,而且东三省就是满洲。
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混淆。
后来弄出溥仪的伪组织,自称满洲国,认为是满洲人统治着满洲,实际上东三省哪可与满洲相提并论?孔子说,名不正,言不顺,清代学者中,就有人主张不用行省或省字,而正名称为布政使司的。
然而总督巡抚又如何称呼呢?所以当时也没有人附和。
然而行省之称到底是不妥,又加说本部十八省,那更荒谬。
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所谓本部非本部之别。
秦代万里长城早已东达大同江,辽河流域永远在中国历史圈之内,如何说它不是中国之本部?这原是外族有意混淆是非造出来做侵略的口实。
此刻又有所谓华南、华中、华北等称呼,试问中国政治区域上,有没有这些分法呢?中国人不注意,大家跟着这样叫,现在还没有事,不要紧,十年二十年以后,说不定政治上,外交上又发生问题。
连我们的脑筋里,观念上,也会发生问题的。
如想我们是华南,你们是华北,这些观念,都会发生很大作用。
这因讲元代的行省,而牵连涉及。
这都该值得我们警惕的。
省区的省字,根本是一个不祥的名称,最好以后能在新的地方政治区域之划分下把这字革除,再不沿袭。
戊、明代地方之监司官与督抚 再说明代地方长官,与承宣布政使并列的,还有一个提刑按察使。
布政使管行政,按察使管司法。
又有一个都指挥使,管军事。
三个司合称为三司。
承宣布政使司又叫藩司,提刑按察使司叫臬司。
清时俗称藩台、臬台。
照理,臬使尚可称台,如御史行台之例。
按察使本该流动考察,不常川驻定一地方。
但明清两代都已固定有驻地,称台已不合理。
至于承宣布政使司,全省行政都归他管,更不该称台。
布政使下面有参政、参议等官,提刑按察使下面有副使佥事等官,这种官派出去,叫分司。
分司到了清朝,俗称道台,普通称为监司官,犹如省政府派几个参议到地方上协助办事。
这样一来,地方政府的事情就更不好办了。
明制,地方行政制度,最低一级是县。
县上面是府和州,这是第二级。
上面才是省,就是承宣布政使司,是第三级。
三级之外再加上分司,就变成了四级。
元代是把中央政府分置到地方,就变成行中书省。
明、清两代是把地方高级政府再派到低级去,这便是监司官。
这也难怪。
因为省区大,事情多。
不得已,才有分司分道之制。
分司分道有分为两种。
由布政使派出的叫分守道,由按察使派出的叫分巡道。
明末大儒王船山,在其所著《黄书》里,曾有一统计,说:山东省有六个府,但有十六个分司。
山西省有五个府,有十三个分司。
陕西省八府,有二十四个分司。
四川省九府,有十七个分司。
这样一来,县上面有府,府上面有司(分司),司上面才是省(司),变成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
县官才是亲民官,府、州之上,都是管官之官。
管民的官不仅少,而且又是小。
所以中国地方政治,宋代已经不理想。
宋制分路,诸路分设帅、漕、宪、仓四个监司官。
明代更不行,一省分成三个司:一个布政使司,一个按察使司,一个都指挥使司。
前两个藩臬二司,又再分许多分守分巡的司。
这许多官下面,才是府、州和县。
县官压得太低太可怜了。
他服侍奉承在他上面的长官还来不及,哪有功夫去亲民。
汉代县上面是郡,郡上面没有了。
汉代的郡太守,是二千石官,阶位俸禄,和九卿相似。
一个县政府,也往往有属吏几百人的大规模。
但汉郡多至一百以上。
今天中国的一省,有比欧洲一国更大,而现在的官场习气,还是薄省长而不为。
至于县长,那真微末不足道,这实在是政治上一个大问题。
以上还只讲的明代的布政使,按察使与都指挥使。
而这几个长官上面还有官,还有更高一级的官,那就是总督与巡抚。
总督巡抚在明代制度下还尚好,因其必有事才派出此等官,并且都带一个都御史的衔。
这就是说,由中央政府都察院的都御史临时派到地方去办事,所办是巡抚、总督等事。
譬如倭寇来了,沿海地方没有总其成的人,就派一个总督或巡抚去,这是临时的。
过几年,事情平定了,这官仍旧回中央,机关也撤销了。
但一到清代,总督巡抚又变成为永久的,在布政使(藩台)按察使(臬台)上面再加巡抚总督,地方行政就愈来愈坏了。
我们现在再从历史演变源头上说来,汉时由刺史变成为牧,以及唐代之十道观察使,这些都是由监察官变成地方行政长官的。
只有节度使才是军事长官变成行政长官,然而还是意在开边对外的。
明清两代之总督巡抚,则是意在对内防乱,不在对外开边。
由中央来临制地方已不好,何况派军官来常川镇压呢?若非地方政治失败,亦何来有此需要?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中国政治史上一大失败。
己、明清两代之胥吏 上面所说,是地方政府一层一层的由上面加来的高压。
而从下面讲,又出了毛病。
最要是骊胥之制。
中国传统政治有官与吏之分,最先吏是指的管理一般业务的,略等于今天之所谓事务官。
在两汉时代,每一机关的长官独称官,属官皆称吏。
官吏的出身,并无大区别。
宰相由吏属出身,是件寻常事。
所以汉代政治风气极敦厚,极笃实。
唐代的吏和官,已分得远了,然而两者间还是没有判然的划分。
判然划分的时期要从明代起。
若再溯而上,弊病仍是先出在元代。
因元代政府长官,都用的蒙古人。
蒙古人不懂政事,而且不识中国字,于是便得仰赖于书记与文案。
中国读书人没有了出路,便混进各衙门当书记与文案去。
那便是官与吏流品泾渭之所分。
但明太祖时,因人才不够用,推行荐举,任何长官都可荐举人才。
所荐举的,不分进士、监生、吏员,朝廷尚是一律任用。
进士等于如高等文官考试的及格人,监生等于是大学生,吏员则等于是公务员。
这时尚不分高下,同样有出身。
但那是一时济急。
迨到明成祖时,便规定吏胥不能当御史,这就是规定曾任公务员的不能做监察官。
又吏胥不准考进士,这样一来,便限制了吏胥的出身。
官和吏就显然分开两途。
于是在中国政治上的流品观念里,吏胥被人看不起。
这一观念始于元,到明成祖时而确定。
这事在中国政治史上,实有甚大的影响。
西方社会有阶级,无流品。
中国社会则有流品,无阶级。
这也是双方社会一大区别。
直到今天,流品观念在中国人脑里还很深。
譬如教书人,是一种行业,衙门里办公文作师爷的也是一种行业,但行业与行业之间,却显分清浊高下,这便是流品观念在作祟。
又譬如文官武官,一样是个官,官阶品位尽相等,但在流品观念下,则文官武官又显然有分别。
这是中国社会独特的传统,西方人不易理解此分别的。
若要把流品二字翻成西方名词也无法翻,只有中国人脑筋里才懂得。
譬如唱戏也是一职业,然而在中国人脑筋里,唱戏的自成一流。
这一流,那一流,各自有品,等级不同。
种田的、读书的,也同样是职业,而在我们脑筋里,除开职业之外,却夹有另一观念,这就是所谓的流品。
在明代政府的观念里,胥吏另成一流品,胥吏是没有出身的。
先是不准做御史,后又不准考进士,结果只叫考生或秀才之中无出路的来当胥吏。
胥吏流品虽低,但他们对当时政治影响却很大。
近代政治界中最有名的所谓绍兴师爷,也不是清代才有,早在元明时代已有了。
他们的势力,早已布满在全国。
明代有一位理学先生陈几停,他有一位朋友到绍兴去当知县,他写一篇文章送行,大意说:天下治乱在六部,而六部的胥吏完全是绍兴人,这些绍兴人虽在中央政府办文案,但他们的父兄都还在绍兴。
希望你到绍兴后,多能注意教化他们的家庭来。
把胥吏的父兄教化好,将来他们就可以教化胥吏。
胥吏变好了,天下就治。
所以绍兴是天下治乱的根本。
陈几亭这番话,实在不能说没有他道理。
历史上的事情,有些摆在桌子面上,有些则隐藏在桌子底下。
一般谈历史的,只注意桌子面上事,譬如宰相怎样,六部怎样,而没有注意到桌子底下一样有力量,一样有影响。
直到晚清光绪年间,还有人这样说:一切事情到了胥吏手里,铨选则可疾可迟,处分则可轻可重,财赋则可侵可化,典礼则可举可废,人命则可出可入,讼狱则可大可小,工程则可增可减。
大抵中国政治界里胥吏所经管的,不外此七项,即铨选、处分、财赋、典礼、人命、狱讼与工程。
其实政事之大者,在当时也只此七项。
吏胥则是此七项的专业人,传统的专门家。
他们是职业政治家而擅有专门知识的。
但当时官场又看不起这些人,这些人也自认流品卑污,因此不知自好,遂尽量地舞弊作恶。
我们都知道,旧官场查复公事,有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也有说查无实据,事出有因的。
照前面报就轻,照后面报就重。
这些都由吏胥上下其手。
明清两代的地方行政官,大都是管官的,不是管事的,事都交给师爷,由吏胥去办。
这种师爷,各衙门都有,上下相混,四面八方相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咸鱼摆烂复婚综艺[娱乐圈]塬
- 钓系咸鱼穿成综艺万人嫌摆烂后水仙乘鲤
- 无限轮回荣光九四或跃在渊
- 管家总被人觊觎[快穿]豆腐军团
- 关小姐又在写情书茴笙
- 反派修为尽失后一丛音
- 离婚后与前夫重生回高中稚棠
- 我转生成了横滨碰瓷王筱潋
- 我在古代当先生北沐南
- 扶桑知我扶桑知我
- 战国赵为王熙檬父
- 墨道归元胡鳕
- 雪下轻卿[先婚后爱]州府小十三
- 业已成魔寒鸦
- 九阳神王寂小贼
- 在古代老干部面前作死后沙舟踏翠
- 原谅她范月台
- 七十年代奇葩一家亲永岁飘零
- 小崽崽又进化了云劫
- 浮锦(双重生)落日蔷薇
- 魔鬼主教远古莱德
- 遮天辰东
- 穿书后我被美惨强反派掰弯了衾寒月暖
- 在柯学世界当小学生魑归
- 星旅人郝景芳
- 我的18岁男房客Antigravity
- 那个主角攻的好朋友士一
- 我在凡人科学修仙洛青子
- 借种生子三年后撒糖小甜饼
- 引诱(志怪1v1 h)渐无书
- 返龙柿子的猫
- 我有一个修仙世界纯九莲宝灯
- 比格犬受害者联盟诸葛菜
- 刑侦专家她在90年代当未成年七七笙
- 银色铁轨京洛线
- [西幻]北道而驰爱因斯弹簧
- 秘密情书[GB]风辞雾隐
- 巅峰学霸一桶布丁
- 我大哥也穿过来了!阿扶光
- 万人迷什么的不要啊(强制NPH)豆沙花卷
- 清纯炮灰连夜跑路喻狸
- 团宠幼崽养成计划凤箫声醉
- 十九世纪换嫁情缘鲜肉豆沙粽
- 我的物品能升级全针教主
- 天崩开局,被发配到边疆当死士萝卜小豆干
- 儒道成圣,但是理科生天天有饭开
- 贼天子漫客1
- 你知道的太多了莫晨欢
- 北域战记五江半岁生
- 学霸的军工科研系统十月廿二
- 退役勇者转职魅魔sanna
- 攻略精灵(西幻万人迷NP)珀长烽(请监督我写文)
- 灵骨被夺?她逆天觉醒神脉杀疯了六六糖
- 反派夫妇改造日常日日复日日
- 豪门社畜不干了乔柚
- 就要做继承人女高别给我撤回(美高np)专业绷带弹奏家
- 欢喜记石头与水
- 野心家(灼灼韶华原著小说)石头与水
- 别人航海,我种田风的铃铛
- 清纯炮灰连夜跑路喻狸
- 诸天伏魔录精神不太好的坐家
- 你吃了吗?一节藕
- 演替半截白菜
- 不是人又怎样[快穿]宴不知
- 做人没必要太正常小狐昔里
- 黜龙榴弹怕水
- 儒道成圣,但是理科生天天有饭开
- 死灵法师在末世疯狂屯兵愤怒的食人鱼
- 人在中世纪,抽卡升爵疯狂的石头怪
- 这读心术不要也罢廿乱
- 重回11岁,我的节操不见了陌迟
- 沧澜仙魔录竹下轻笛
- 玩家是心灵导师才不是第四天灾!玉食锦衣
- 寻宝全世界行走的驴
- 星际兽世用歌声治愈狂化一春
- 军工大院女儿奴[年代]浣若君
- 欢喜记石头与水
- 魔王梵阖[西幻]南崽崽
- 前夫哥,但万人迷颂图
- 在西汉庖厨养娃万重泉
- 美莉栗优
- 十九世纪换嫁情缘鲜肉豆沙粽
- 做人没必要太正常小狐昔里
- 冰之祭礼未名月下
- 这读心术不要也罢廿乱
- 气域传说之战神再起孤城半山
- 沧澜仙魔录竹下轻笛
- 重燃2003万古青天一株柳
- 萤火之春(修仙NPH)甜酒酒。
- 超级游戏升级召唤系统风轻阳
- 从马桶间开始弎夜
- 穿回古代卖盒饭(美食)桔梗猫
- 我!清理员!鱼狱圄
- 你也想养小恶龙吗?凤箫声醉
- 叶阳大人升职记天谢
- 鉴昭行南月知清
- 成婚前你不是这么说的!松庭
- 守寡多年[星际]芝芝猫猫
- 一路放晴猫猫可
- 《吸血鬼骑士》寂结芳华紫幻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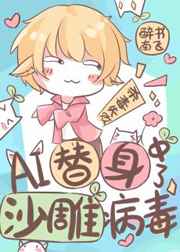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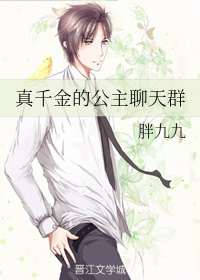
![哥谭梦游记[综英美]](https://www.xtolly.com/img/12450.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