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楔子(2/5)
的失败——卢森堡正是这一党派的成员。
但我们同样不应忘记,她所遭受的牢狱之灾,多数是由于她的反战主张:第一次在1915年,由于煽动公众反对政府决议,她被囚禁一年。
而在刑满之后,无休止的非法拘留、“预防性监禁”成为政府阻止她活动的手段,并一直持续到“一战”结束。
事实上,对于斯巴达克派的起义,卢森堡持有的是谨慎支持的态度。
她不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是面对一个屡战屡败、背负屈辱的德国,倘若没有一股新鲜的、充满正义的力量注入其中,那些复辟的、盲目的爱国主义必然会乘虚而入,导致整个国家陷入更加疯狂的境地——譬如对一个名叫希特勒的人的坚定支持。
“这是个愚蠢的骗局,”她在自己服刑期间撰写的反战小册子《尤尼乌斯》[2]中这样写道,“去相信我们可以像兔子那样,在暴风雨来临前躲起来,等到一切结束后还可以再继续以自己往常的步子走在老路上。
”她预言,德国人不会从失败中学到任何有益的东西,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到了1930年,戈培尔有关“是犹太人让我们蒙受了‘一战’失利的屈辱”的宣讲,还是得到了当时民众的广泛支持,与卢森堡生活的时代相比,他们的信念并没有太多改变。
夏洛特·萨洛蒙的意义,可以被她的后继者们公正地评价。
这位犹太女画家对复调式绘画[3]的预见和诠释,使她几乎凭一己之力将绘画艺术的发展引领到了一个全新的层面。
她不朽的作品《人生?如戏?》(Life?orTheatre?)不仅是绘画史上的重要作品,同时也是对德裔犹太人在“二战”期间遭遇的苦难的一份忠实记录。
她用一幅又一幅的水粉画,描绘了自己在这黑暗岁月里的境遇。
而这部创作于她生命最后几年里的作品,直到她死后多年才得以结集问世。
她是在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被杀害的,但或许,将她的作品全然归入大屠杀纪念中展出或许是个严重的错误。
事实上,夏洛特卓越创造力的意义,要远胜于她作为一名“大屠杀死难者”的价值。
《人生?如戏?》的配色是极艳丽的,这使得画面通常看起来很刺眼。
而这种不同寻常的风格,似乎暗示了她所处的境遇——一面是压抑与禁锢,而于自己,夏洛特·萨洛蒙的才华却不容许半点儿压抑。
这组矛盾的结果,最终通过这些非凡画作得以呈现。
它们贯穿了绘画者在两次大战中的经历,将其间的疯狂与痛苦小心收纳,并以鲜艳的界限,诠释此时与彼时生命的痛楚和希望。
夏洛特的创作是“不顾一切”的(尤其是对纳粹所强调的“进步文艺规范”),这是来自评论者的观点。
尽管她的追随者们几乎奉她如神明,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地位绝不夸张。
《人生?如戏?》在表现形式上具有混合性的内在处理,在第一页便以三色字体的“歌剧”[4]命名,还出现了一组代替“演员表”的文字。
而接下来的每一页,除了色彩明艳的图画,图画上同时还出现了文字与乐谱,使欣赏者可以在欣赏画面的同时,“聆听”不自觉流入头脑中的旋律,从而使作品以一种“纸上歌剧”的形式被欣赏。
她是在法国南部的里维埃拉完成这些作品的,尽管欧洲大陆此时正危机四伏,但那里当时还是在意大利人的“友好保护”之下。
可仅仅在完成作品后不久,夏洛特便遭遇了被驱逐的命运。
根据一份可信的报道,夏洛特在作画时会面朝大海,嘴里哼着歌——这大概也是她的作品富于韵律感的一个原因。
欣赏她的作品是一种多层面的体验。
随着黑暗渐渐渗入她的生活,她在画布上的表达也随之发生改变。
由于她富于表现力的手法,欣赏者不难像置身诗歌朗诵会或是音乐会上那样,体察作者心境的变化。
这种将声音与画面结合的表现方式同时还具有独一无二的“紧迫感”——画布上的角色仿佛可以主动发声,央告人们来查看这里发生了些什么。
对于欣赏者而言,他并非从《人生?如戏?》中听到或看到了一些什么,而是直接进入了夏洛特所表现的那个世界。
存放这部作品的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历史博物馆通过现代技术,将夏洛特的杰作搬到了互联网上。
人们通过访问这个网站,便可收获有关《人生?如戏?》的全方位视听体验。
夏洛特将绘画与音符融合的尝试,使她逃离了恐怖的深渊——这深渊既是来自他人的暴行,同时也来自自我。
她的天赋使她可以驱散笼罩在自己生活之上的黑暗,同时揭露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共谋”。
《人生?如戏?》始于1913年她的姨妈自杀的那个晚上,那同时也是“一战”前夕看似安宁的一天。
但死亡往往孕育着全新的生命——在自己的姐姐离世之后,夏洛特的母亲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来到“一战”前线,成了一名战地护士。
而正是在那里,她遇见了萨洛蒙医生。
两人迅速相爱,结婚,生下了夏洛特,而“夏洛特”这个名字,正是来自她不曾见面的姨妈。
可这个美丽的名字,却暗示了一个不祥的结局,而这个结局在夏洛特降生时似乎已经被人们察觉:“小夏洛特生下来,似乎就带着对生活的不满。
”而夏洛特父母的婚礼在后来的研究者们看来似乎也并不寻常:“那里似乎没有什么迹象显示,一场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尽管事实如此。
”夏洛特的出生伴随着秘密与谎言。
而从一开始,她便试图引导自己的观众去关注那不寻常的东西: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它的国民是怎样经营自己的日常生活的,那是一种狂喜与愤怒、冷酷与压迫共存的状态。
与此同时,犹太人也背上了奇怪的罪名——由于他们的相对较高的自杀率,其他人开始将“堕落”的帽子扣在他们头上——自杀是亵渎神明的表现。
出于这样的原因,夏洛特姨妈的自杀,只好被家人掩盖起来。
但事实上,萨洛蒙家族总共有七人死于自杀,包括夏洛特的母亲——她于夏洛特八岁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夏洛特则被告知自己的母亲“死于流感”。
根据记录,在这一时期,“没有人告诉过夏洛特自己家族这些死亡事件的真相”。
尽管尚无从知晓自己的“宿命”,但夏洛特还是为自由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在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便想象自己好像一只被束缚的飞蛾,“只有靠近烈火才能挣脱枷锁”。
而当她在二十三岁时得知自己家族的秘密后,想到自己可能也难逃自杀的诅咒时,她决定要做些什么。
“务必保存好它们,”在完成自己的作品后,夏洛特将它们交给了自己的朋友莫迪斯医生,“这是我全部的生命。
”[5]当她坠入黑暗的深渊时,勉强用画笔描绘出那不可言说的可怖景象,使她成了那个时代的记录者。
这是她谋求“幸存”的方式——生命可以轻易被磨灭,可记忆却能永存。
而在这一层面上,她又是个不折不扣的榜样。
和罗莎·卢森堡,以及我们即将谈到的玛丽莲·梦露一样,夏洛特·萨洛蒙全力以赴,对抗这世界,以及自己内心最不安的情状。
这恰恰也是我试图论证的关键部分——只有当我们对她们所遭受的苦难有所体会与认同时,这些杰出女性的意义才能真正被理解。
你永远无法在一场战争中装聋作哑,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或者提高耳机音量——像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做的那样,去掩盖由远及近的隆隆炮声。
在多数时候,按照官方辞令的说法,“战争让女人走开”,她们至少可以做一个无能为力的旁观者,等待灾难降临或风平浪静,但由于自己难以隐抑的才华,夏洛特却成了一个“主动受难者”。
按照夏洛特的老师,同时也是她曾深爱过的男人阿尔弗雷德·沃夫森的说法,夏洛特是“亲近死亡”的,这与她的家族成员,以及她所属的那个时常忘却死亡的教训并主动发动战争的罪恶国家对待死亡的态度截然相反(沃夫森是一位“一战”幸存者)。
他曾对夏洛特早期画作《死亡与少女》(DeathandtheMaiden)做出过这样的评价:“从对少女动人的表现来看,死亡并没有对她造成如通常一般的威胁。
它甚至表现得如此温柔、亲切、不堪一击。
” 对于女性而言,她们习以为常的“畏惧”,带来了怎样的“报偿”?这对于今天的女权主义者而言仍然是一个关键性问题。
如果女性的畏惧来自她们的生活本身,那也一定是一种“被强加”的体验。
在2011年英国伯明翰开办的一期以女权主义为主题的夏季学校中,女权主义者艾米莉·伯肯肖表示自己并不喜欢“真相”,“那更会使我感到害怕”。
畏惧并不只是一种信号,它甚至可以成为一种需求。
女人们不得不感到害怕。
伯肯肖谈论了女人们在街上可能遇到的危险——那些穿着过分性感的女孩被看成一种隐患,以至于她们甚至要为自己遭受侵害承担一部分责任。
但她的演说也出色地捕捉到了这种畏惧的模糊性:女性对突如其来的暴力的“通常反应”,暗示了人们对女性的某种期待(懦弱、无力,伴随着一些有关“弱不禁风”的陈词滥调)。
如果女性一旦表现出潜在的“攻击性”,她便会被视作异类,毕竟根据多数人的臆想,女性并没有办法保护自己,更无法进行“攻击”了。
使女人常常处于恐惧之中,显然会增长男性的权威性与安全感。
这似乎是一个关于世界的根本性问题:这世界本不像人们描述的那样危机四伏,而恐惧也不应当成为某类人的生存常态。
而当我们将恐惧视作一种必要的本能时,它将会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上烙下印记,成为一种无法回避的集体认同。
对于罗莎·卢森堡、夏洛特·萨洛蒙和玛丽莲·梦露来说,恐惧是她们的“亲密朋友”。
由于时常与威胁相伴,她们有关恐惧的经验,更像是一种超自然的能力,或是一种特异的知识,使她们有足够的能力来忍耐可怕的黑暗。
可是我们为何一再地谈论战胜恐惧的经验,而不去追究制造恐惧者的罪责呢?我们或许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一战”后的德国人,并没有反省自己挑起战争的责任,反而继续酝酿了下一场战争。
从恐惧的角度来看,德国人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们并没有从自己的内心解决自己无法摆脱的恐惧,而是一味地希望可以将恐惧转嫁到别人身上。
他们甚至不承认自己内心的恐惧——当一个人(经常地)或一个民族(反复地)否认现实,转嫁危机,显然是很可怕的事情。
当夏洛特抵达奥斯维辛时,她已经怀有五个月的身孕了。
她的传记作者玛丽·洛文塔尔·菲尔斯蒂娜指出,在奥斯维辛,女性往往会先被处决(在奥斯维辛的幸存者中,仅有17%是女性,而通常来说女性忍耐极端条件的能力似乎更强),而孕妇的命运则要更加悲惨,根据目击者的报告,怀孕的女人们往往会被以“提高待遇”的名义从队伍中率先被挑出来,随后就会被处决。
“种族灭绝,”菲尔斯蒂娜这样写道,“总会将妇女和孩子放在‘优先’的位置。
”这看似有些令人震惊,却道出了这样的事实:对于敌人来说,女人可以孕育生命的能力是他们最大的恐惧。
这种恐惧并非来自怀孕与出生的动作本身,不同于女性主义者用来反驳弗洛伊德那声名狼藉、被看作对女性最严重的诽谤的“阳物崇拜”理论(没有比站在男性视角对女性进行“精神分析”更可耻的欺诈了)的“生殖嫉妒”;并非由于男性对自己那孕育他们生命的身体因亏欠而产生的憎恨;也并非由于受孕意味着所有女人只能,或必须成为母亲,或者是更有争议的观点:这违背了女性原始的自我认定。
问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色令智昏刘水水
- 咸鱼摆烂复婚综艺[娱乐圈]塬
- 吃瓜贵妃的自我修养暗香
- 撩肾达人/万千荣光甜醋鱼
- 青梅竹马文里的女配东家宁
- 剑啸灵霄流浪的蛤蟆
- 怯懦万人迷美而自知以后君幸食
- 离婚后与前夫重生回高中稚棠
- 超神宠兽店古羲
- 你是不是输不起柒曲
- 大院二婚妻[八零]青雨梧桐
- 扶桑知我扶桑知我
- 大宋有毒第十个名字
- 窈娘春未绿
- 重生东京黄金时代安静的想
- 九阳神王寂小贼
- 身为女王如何拒绝爱意吾九殿
- 大唐不良人庚新
- 在夫妻综艺自曝离婚后池多鱼
- 春宫抱空山
- 反派他早亡的妻子重生了冬十四月
- 成为虐文主角后她咸鱼了虞宵
- 苗疆蛊事2南无袈裟理科佛
- 星际第一濒危向导璃子鸢
- 新来的转学生强到炸裂晚秋初十
- 在全A男团中假装Alpha星期十
- 没关系,快带我走一江听月
- 超进阶复制夭厌
- 天降萌宝霸道总裁找上门沐晴天景司寒免费阅读
- 我妈是年代文早逝原配芷柚
- 安全屋生存指南[无限]青鸟宴
- 婚夜温柔一枚柚
- 我能看见宝物打鼠高手
- 特工枭医狂妃雪鸾歌
- 贵族男校里的路人老师灼云衣
- 西游之我成了齐天大圣滋滋作响
- 藏锋吕铮
- 重生后,我成了奸臣黑月光偏方方
- 天神古帝应不住流风
- 夫君的遗腹子自带口粮将月去
- 诱他习又
- 貂珰冻感超人
- 中间商赚差价,全民求生lesliya
- 清平梦华录非天夜翔
- 成学霸了,你说你是大明星系统路行则
- 天幕剧透我是太宗织鹊
- 锦衣行(白衣公卿原著小说)扶兰
- 半熟(遇人不熟原著小说)在言外
- 钢铁蒸汽与火焰树岚
- 师父心塞九鹭非香
- 异界之三国群英传灭世小苹果
- 跳诛仙台后,穿进兽世种田文当稀有神兽花相芍芍
- 我被困在方块之中狂喜
- 我的第一篇茂灵:師父養成黑猫坏坏
- 在全A男团中假装Alpha星期十
- 大汉女侯峨眉山猴子03
- 青剑宗修行纪事趴在墙头看桃花
- 安全屋生存指南[无限]青鸟宴
- 攻略精灵(西幻万人迷NP)珀长烽(请监督我写文)
- 当猎豹穿成奥运冠军马猴烧酒鱼
- 藏锋吕铮
- 天神古帝应不住流风
- 西江的船玖月晞
- 在男团成功出道后择桉
- 欢迎来到灵师学院伸出圆手
- 纯阳圣体新晋
- 半熟(遇人不熟原著小说)在言外
- 蜀山掌门系统扶摇先生
- 谍报上不封顶桑栀栀
- 花常好月常圆人长久(花好原著小说)亦舒
- 御兽:我契约的猪是转世大能悠然醉酒
- 挽舟渡溪南妧念
- 和妻子重生回退婚前春枝晓
- 天才俱乐部城城与蝉
- 觉醒在龙珠世界不落之阳
- 守寡多年[星际]芝芝猫猫
- 超进阶复制夭厌
- 沐晴天景司寒沐晴天景司寒免费阅读
- 我妈是年代文早逝原配芷柚
- 青剑宗修行纪事趴在墙头看桃花
- 当猎豹穿成奥运冠军马猴烧酒鱼
- 贵族男校里的路人老师灼云衣
- 重生后,我成了奸臣黑月光偏方方
- 森林里的辛德瑞拉[西幻]何棋
- 政敌驯养指南 1v1 H好吃今天吃什么
- 老婆要慢慢养凛春风
- 中间商赚差价,全民求生lesliya
- 大小姐,请收下我[GB]先天下之喵而喵
- 成学霸了,你说你是大明星系统路行则
- 请扮演渣女[快穿]酥小酒
- 半熟(遇人不熟原著小说)在言外
- 蛇劫(志怪,人外1v1)羽痕
- 光明神想当我情人[西幻]繁星春
- 觉醒在龙珠世界不落之阳
- 小芳出嫁伊北
- 人在古代,躺平开摆桃梨不言
- 幻想怪能礼堂绅士
- 性转:这个修仙界的男人不对劲顾小白丶
- 阎王的生死簿有点可爱神喃
- 吞没泡泡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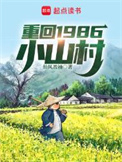


![哥谭梦游记[综英美]](https://www.xtolly.com/img/12450.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