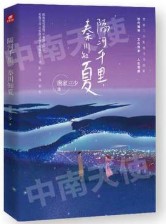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一部 4(4/5)
快就会怎么叫你吗?‘调情小姐’!” 调情小姐!我真是哭笑不得。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问她。
“因为事实就是这样。
”她似乎瞬间变得愠怒,“如果我知道你穿上这件裙子只会跟人调情,就不会送给你这么漂亮的衣服。
” “哦!”我重心不稳地跺了跺脚,我猜自己也醉得和她差不多了,“哦!”我把手指插进晚礼服的领口,想要解开扣子,“你要是想要回去的话,我现在就把这该死的裙子脱下来!”我说,“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 听到我这么说,她又向前一步,抓住了我的胳膊。
“别犯傻。
”她的语气有些缓和了。
我挣脱了她,继续脱衣服,但是白费力气,因为喝了酒,加上又惊又气,我的动作十分笨拙,怎么都解不开裙子的纽扣。
姬蒂又抓住我,很快我们就几乎要打起来了。
“我不允许你说我卖弄风情!”她抓住我的时候,我说,“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你怎么能这样?如果你知道——”我把手伸进领子,她的手盖住了我,她的脸向我靠近。
看到这一幕,我立刻感到一阵晕眩。
我以为我已经成了她的姐妹,正如她期望的那样。
我以为我那压抑着的诡异欲望已经冷却消失了。
现在我只知道她的胳膊环绕着我,她的手握着我的手,她的呼吸在我脸上发热。
我抓住了她,不是把她推开,而是把她拉得更近。
我们渐渐不再扭打,而是变得安静,我们的呼吸乱了,心也怦怦跳。
她的眼睛睁得很大,像墨一样黑,我感觉到她的手指离开了我的手,移向我的脖子。
突然,走廊里传来一阵响动和脚步声。
我怀里的姬蒂像是听到枪响一样吓了一跳,赶紧迅速往后退了几步。
一个女人——魔术师的助手埃丝特出现在门廊的另一边。
她脸色苍白,神情严肃。
她说:“姬蒂,南,你们相信吗?”她拿出了一块手绢,用嘴咬着,“刚才来了个男孩,从查令十字街医院来的。
他们说格利·萨瑟兰在那里”——就是那个和姬蒂一起在坎特伯雷游艺宫表演的喜剧歌手——“他们说格利在那里——他喝醉了,开枪自杀了!” 这是真的——第二天我们都听说了这个可怕的真相。
我不用去怀疑,因为来伦敦以后就曾听闻格利是圈里公认的酒鬼。
他每演完一场都要在回家路上去酒吧喝一杯。
我们举行派对的那天他在富勒姆[25]喝酒,坐在一个角落的凳子上,听到坐在吧台的一个人说格利·萨瑟兰已经过了全盛时期,应该给更有趣的艺术家让路了。
他说他看了格利最近的演出,觉得那些梗都不好笑。
吧台服务员说格利听到这些话就跑去和那个男人握手,给他买了一杯啤酒,然后给所有人买了啤酒。
跟着他回到家就拿出一把手枪,朝自己的心脏开了一枪。
我们在马里波恩那天晚上并不知道这些,只知道格利一阵痉挛,然后就离开了人世。
但是这个消息结束了我们的派对,大家都像埃丝特一样紧张而悲痛。
听到这个消息,我和姬蒂跑回舞台上,上楼梯的时候她抓住了我的手,但我想这是因为悲痛,而非出自温暖。
经理让大家把所有的灯都点亮了,乐队也把乐器放在一旁。
有些人哭了,那个刚才挠我的短号手抱住了一个发抖的女孩。
埃丝特哭着说:“哦,太可怕了不是吗,太可怕了!”我想大概是因为喝了酒,大家感受到的冲击更大了。
然而,我不知该作何感想。
我完全无法思考格利的事情,我的思绪还在姬蒂那里,在更衣室的那一刻,当我感觉到她的手在抚摸我时,我感觉到我们之间进了一步。
那之后她就没再看我,现在她跑去和那个带来格利自杀消息的男孩交谈。
然而,过了一会儿,我看到她摇着头走开,似乎是在找我,当她看到我在舞台侧边的阴影里等她的时候,走过来叹了口气说:“可怜的格利。
听说他射穿了自己的心脏……” “我想起来,”我说,“正是因为去看格利,我才第一次去了坎特伯雷,然后见到了你……” 她看着我,颤抖起来,一只手托着腮帮,满面愁容。
但是我不敢上前安慰她,只是痛苦而惶惑地站在那里。
当我说我们该走了的时候——因为其他人都在陆续离开——她点了点头。
我们回到更衣室拿外套,漆黑的屋子现在亮起来了,脸色苍白的女士们都拿着手绢擦眼睛。
然后我们到后台入口,等着看门人叫的马车过来。
好像等了一个世纪那么久。
凌晨两点我们才坐上回家的马车,在各自的座位上沉默不语,姬蒂只是时不时重复着:“可怜的格利!为什么会这样!”我依然酩酊,依然晕眩,依然被绝望的激情驱使着,但也依然迟疑不前。
这是一个寒冷而美丽的晚上,我们离开了派对的人群,街上十分安静。
路上雾气深重,还结了冰,我时不时感受到马车轮子的倾斜,听到马步的打滑声和马夫的咒骂声。
街上的冰霜反射出光亮,雾中的街灯散发着黄色的光晕。
走了很久,我们都是街上唯一的一辆马车。
这匹马、车夫、姬蒂和我可能是这座沉睡的石与冰的城市中唯一醒着的生物。
最后我们上了朗伯斯桥,姬蒂和我几周前还在这里看桥下的游船。
现在我们的脸贴在车窗上,看着一切都变换了和白天不同的模样——那堤坝上的灯像一串琥珀珠子一样消融在夜色里,议会大厦投下锯齿状的巨大阴影,在河面上若隐若现。
泰晤士河上的船只安静地停泊在那里,灰色的河水浑浊而黏滞,看起来十分诡异。
这一幕让姬蒂拉下窗户,用兴奋的高音呼喊着,让车夫停下来。
然后她推开了马车的门,把我拉到了大桥的铁栏杆前,抓住了我的手。
“看。
”她说。
她似乎完全忘记了悲伤。
在我们脚下的水中,有一块块六英尺长的冰块在水流中漂着,就像晒太阳的海豹。
泰晤士河正在结冰。
我的目光从河水转向姬蒂,又从姬蒂转向我们站着的大桥。
我们身边除了车夫没有别人,他竖起了斗篷,遮住耳朵,往烟斗里装上了烟草袋。
我又朝河面看去,看着那伟大而平凡的变化,如此轻易就屈从了自然的法则,却又稀奇而令人不安。
这就像是一个只为我和姬蒂出现的小小奇迹。
“一定很冷吧!”我轻声说,“想象一下如果这一整条河都结冰了,从这里一直到里士满。
你会从河上走过去吗?” 姬蒂颤抖着,摇了摇头,“冰会裂开的,”她说,“我们会沉入河里淹死,不然就是搁浅,冻死!” 我以为她会笑,而不是给出一个认真的答案。
我仿佛看到我们两个在一片比煎饼大不了多少的冰上,随着泰晤士河流向大海,也许还经过了惠特斯特布尔。
这匹马向前迈了一步,缰绳发出了叮当声响,马夫咳嗽了一声。
我们仍盯着河面,不说话,也不动,最后我俩都感到悲伤。
姬蒂终于对我耳语:“是不是很奇妙。
” 我没有回答,只是盯着浑浊的河水,它们打着漩儿,不情愿地从我们脚下的桥柱上流过。
但是当她再次颤抖时我向她跨出一步,感觉到她也向我依偎过来。
桥上寒冷刺骨,我们可以回到铁栏杆那里,躲进马车,但是我们都不想离开这结冰的河,或许,我们终于发现不想离开的,是彼此的体温。
我抓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在手套里僵硬冰冷。
我把她的手放在我的脸颊上,也没有把它暖热。
我的眼睛一直盯着桥下的流水,然后解开了她手腕的扣子,脱下了她的手套,把她的手指放在我的唇边,用我的呼吸让它暖和起来。
我轻轻朝她的指关节叹了一口气,然后把它翻转过来,朝她的手掌吹气。
除了河上的波浪,再没有什么别的声响。
然后,她用低沉的嗓音说:“南。
” 我看着她,她的手还举在我的嘴边,我的呼吸仍温暖着她的手指。
她的脸朝向我,目光深邃而奇特,就像我们脚下的流水。
我把手放了下来,她的手指还在我的嘴上,然后她慢慢地把手指滑向我的脸颊、我的耳朵、喉咙和脖子。
她的面容颤抖了一下,对我耳语:“你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对吧,南?” 我想我叹了口气,叹气是因为知道,终于,有需要保守的秘密了!然后我把脸贴近她,闭上了眼睛。
一开始她的嘴唇很凉,然后变得温热——那对我来说,似乎是这整座城市里唯一温暖的东西了。
过了一会儿,她迅速看了一眼我们那个缩成一团的车夫,当她把嘴唇移开的时候,我的嘴唇又湿润又酸痛,赤裸地迎着一月的寒风,好像被她的吻带走了温度。
她把我拉进马车的阴影里,这样我们就不会被人看见了。
我们又靠在一起亲吻,我的双臂环绕着她的肩膀,我感觉到她的手在我背后颤抖。
从嘴唇到脚踝,透过外套和礼服的层层累赘,我感觉到她僵硬的身体贴着我的,我胸口贴近她的地方怦怦直跳,还有我们臀部贴近之处的脉搏、体温和缝隙。
我们就这样站了一分钟,或许更久,然后车夫调整了座椅,马车发出了一个声响。
姬蒂迅速站开了。
我的手还没有从她身上拿开,她握着我的手腕,亲吻着我的手指,发出了有些紧张的笑声,对我耳语:“你把我吻得丢了魂!” 她坐进了马车,我也跟着她爬进去,浑身颤抖,头晕目眩,我想这是因为激动和渴望。
马车的门关上了,马夫唤了小马,马车颠簸了一下,开始蜿蜒前行。
冰冻的河流留在我们身后,和刚刚发生的奇迹相比,它显得如此暗淡! 我们并肩坐着。
她再次把手放在我的脸上,我颤抖了一下,下巴在她的手指上跳动。
但是她没再亲吻我,而是把脸靠在我的脖子上,因而我触碰不到她的嘴,但我耳朵下面的肌肤感觉到了她嘴唇的热度。
她那脱下手套的手洁白而冰凉,滑向我外套前面的空隙。
她的膝盖紧靠着我的,当马车摇晃起来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她的嘴唇,她的手指和大腿变得更沉重,更烫人,和我贴得更紧,让我真想在她的亲近下扭动并叫出声来。
但是她没有对我说话,也没再吻我或者抚摸我。
我只是无辜而畏缩地静静坐在那里,而她似乎也希望如此。
因此,从泰晤士河到布里克斯顿的这一路是我经历过的最美妙也最糟糕的旅程。
最后,马车转了个弯,慢慢停下,我们听到车夫用马鞭的尾部敲了一下车顶,告诉我们到家了。
因为我们太安静,他可能以为我们睡着了。
我依稀记得我们是怎么进入邓迪太太的屋子的——摸到了门钥匙,爬上昏暗的楼梯,进入了这所安详熟睡的房子。
我记得我们停在天窗下,看见一片渺小而闪亮的繁星,姬蒂俯身开门的时候,我静静地把嘴唇贴近姬蒂的耳朵。
我记得她怎样关上了我们身后的门,叹了口气,然后再次靠近我,将我拉近。
我记得她不让我站起来点燃煤油灯,而是拉着我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摸进卧室。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娇藏狂上加狂
- 她是男主好兄弟发电姬
- 杏花如梦作梅花王世颖
- 摘星2林笛儿
- 组织部长3大木
- 万人迷美人受把我攻了[穿书]安喜
- 爱豆家里有道观言朝暮
- 算命师在七零醉该玩死
- 太子失忆后被我拱了慕如初
- 悍妇她来抢男人了金珠玉豆
- 同学录书海沧生
- 婚途脉脉笛爷
- 学完自己的历史后我又穿回来了荔箫
- 儒道至圣永恒之火
- 反派他过分阴阳怪气[穿书]从南而生
- 法师乔安程剑心
- 当天才遇上穿越女/天才的自我修养苏家木偶
- 入骨娇宠烟云绯
- 穿成年代文里的前任小姑夜斩白
- 穿成反派后她只想咸鱼七杯酒
- 纯阳剑尊一任往来
- 神话降临如履
- (综漫同人)当人类最强转生成狗老肝妈
- 相公是男装大佬兆九棠
- 贵妾之女君子迁
- 荒野直播:我的秘境通现代夜深星落
- 尘世之中:觉醒都市超神系统寒星落尘
- 新月生晕(强制NP)棠梨花楹白杨树
- 编织幻境(1v2)蜡笔小di
- 短耳兔被狼族上将盯上了沃木
- 虐文男主的小心肝不好当载酒宿云
- 我在乡下有栋楼猫眠儿
- [综漫] 酒厂魅魔,在线○○椰果栗
- 小傻子和阴鸷反派联姻后时已晚
- 地下城boss刷新中[穿书]鹿林枫
- 二度回归乌诺Uno
- 两个龙傲天遇上后游水之双
- 退婚嫁给书生做夫郎后山间柳
- 莲绝天下玉如初
- 重生之垂暮权倾无尘扬子
- 九龙战神:我的枷锁是星辰有余君
- 我的细胞能修炼浪漫萌萌
- 凡间修神笔尖上的故事
- 都市之全能概念大师喜欢黑小豆的姜文
- 深渊下的红唇温婉如曦
- 都市镇妖使麒麟佛爷
- 超脑武尊吃不吃番茄皮
- 重生后,我的乡贤之路重楼千仗
- 真名代码108件神器的暴走日常未来不是我
- 在每一个梦醒时分花前灯火
- 敢用预制菜?我直播溯源中央厨房念旧歌
- 重返大学:你们管他叫贫困生?秋收十月
- 确诊绝症后,我成了旅行区顶流琢砚冰
- 乐坛妲己是男人?粉丝们彻底疯了百笑
- 你说你学完医就回我消息元一乙
- 予你念平安(叔侄)偷走月亮
- [HP] 你是少爷第一个带回家的女人重九昼
- 残次O切除腺体后钺吟
- 有萤曈曈(古言)秦因
- 荆棘的鱼许焱月
- 太懦弱就要被强制爱沉万安
- 离轨(1v1H)馥柠
- 專情總裁處處寵六月蓉生
- 出轨后被情夫逼着离婚千夜孤舟
- 他的掌心(1v1h)阴雨连绵
- 欲笼(强取豪夺1v1)黑尾虎
- 落日斑斓 (H)一枝酸梅
- 心之全愿华木有听
- 松山书院绯闻事件(古言,NPH,骨科,父女)晓风拂柳
- 采薇(产乳 NPH)霍饭饭
- 金属牙套【骨科gl】n君
- 龙躯x云帆x
- 箭破苍穹:无敌从肝基础箭术开始马铃薯炖牛腩
- 都重生了,当个海王怎么了许诺宝宝
- 神域:我的脑袋里住着大佬顶峰上的穷神
- 路灯下遇见你云林虎
- 系统剧情绑定了我的手机咸鱼之怒
- 你说你学完医就回我消息元一乙
- 失忆沦陷楼兰是
- [HP] 你是少爷第一个带回家的女人重九昼
- 天庭公务员砚栖飞
- 和豪门大佬联姻了微简
- 都陆地神仙了,还抢我奶茶?兰慕闫
- 抗战风云:铁血逆袭愚拙夫子
- 龙躯x云帆x
- 此生不如不见柠檬何时甜
- 月光下复活的她唯我独醒笑傲天下
- 这方寸间,我如神明,主宰一切!猕猴没有桃
- 灵气复苏,开局觉醒灵根金神小火肚子痛捏
- 娇妻系列短篇合集千樱樱
- 北城过风雪(高干1v1)小舟飘飘
- 娇软男O[女A男O]拾酒
- 猛虎嗅蔷薇萤灵
- 生来好色一零九六
- 穿成猫后,我靠破案爆红了三三久久
- [网王同人] 听说迹部暗恋我见天京
- 牛马人南粤帅奇门
- 终南山的修仙日常书海飞尘
- 白龙潭秋风473
- 都市仙尊:从凡尘到九天道尘道人